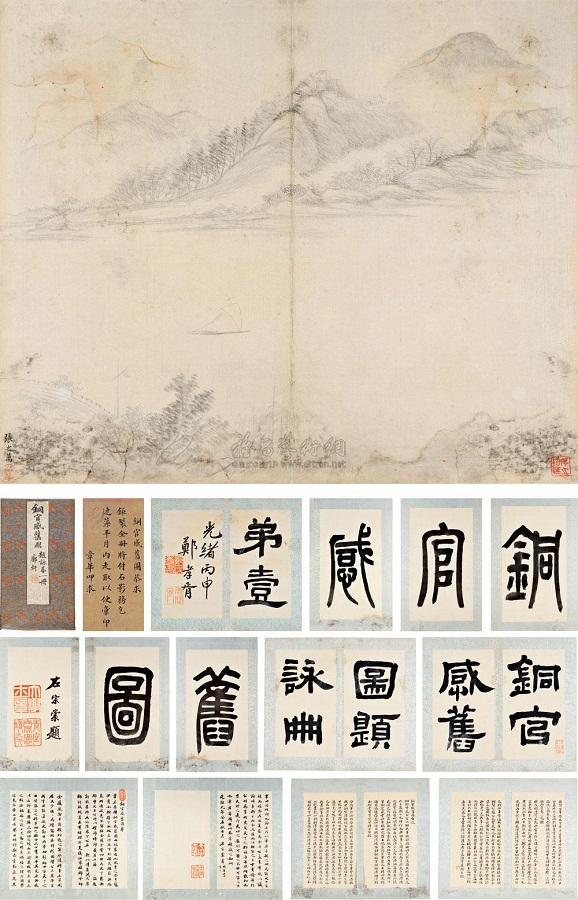本来不在这个blog搞转贴,转载都放在博客大巴。今天去看,突然发现隐藏了很多帖子,说有敏感词汇。其实,那些帖子都是论文、史料,个别词汇或不免敏感,内容肯定健康。草木皆兵,一至于斯,可叹。当然,不是叹博客大巴。李零先生这封信原载《何枝可依:待兔轩读书记》(三联书店,2009年),OCR录入。
本文是应《中国学术》编辑部之请,按例行规定写给田晓菲女士的读后回应。为了不干扰读者对田文的阅读。我一直没有发表此信,现在收入此集,作为历史记录。田晓菲投寄《中国学术》的文章,题目是《学术“三岔口”:身份、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》,最后发表于《中国学术》2001年2期,请参看。
田晓菲女士:
尊作《学术“三岔口”》由刘东先生转来,我已仔细拜读。谢谢您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和关心,并就拙文的基本立场和英译质量提出批评。我听说,您已经把我组织的译介与刘东先生的文章一起列为您的课堂教材(可能是反面教材吧),而且罗泰教授的学生告诉我,他们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(我想一定也有很多尖锐批评)。这是令人欣慰的。因为在我看来,引起讨论本身就是我的目的,更何况,您还提供了另一种阅读立场。虽然我并不赞同您的很多看法,特别是您对整个争论的基本估计,但我认为您的立场确实有一定代表性。如果我没说错的话,您所采取的立场,其实就是留学生中十分常见,因为身处中西学术之间,所以自信超越对立,往往左右开弓,先批外后批内的那种立场。当然,这并不等于说,所有的留学生都和您是一个观点。我是把它归入两支“亚汉学”中更偏向西方学术的一支,您不爱听。它使我比较容易理解,您为什么更同情、理解和支持巫鸿先生,并倾注全力为他本人也为广义的西方学术辩护,比如美国是言人人殊呀,贝格利谁也不代表呀,巫鸿教授才是主流呀,英语不好的“本土学者”李零,他还妄谈什么西方学术呀,等等。
请让我用比较直白的话讲一下我的读后感,而且是废话少说,直奔主题。
首先,我有一个判断,不是价值判断,而是事实判断,即我们的西方同行,我是说直接的同行,他们的研究,即通常泛称为“汉学”的那种研究,和国内的研究,您叫“本土学者”的研究,在很多方面都大不一样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和刘东先生有相似的看法。我们且不管这种差异是由什么造成,比如中国学术的“先天痼疾”,或它的“歪嘴念经”,或它的学术水准“赶不上趟”,或它对西方挑战的“过于敏感”和“不良反应”,但有一点比较清楚,就是这种差异并不是用谁幻想的“国际学术”可以抹平,也不是凭您强调的“个体差异”可以化解,否则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争论呢。在我看来,差异的存在是不是因偏见而引起(我看是原因之一),这是一回事;而它本身有没有(我看是有),这是另一回事。如果您连这种差异都不承认(您说中西学术的不同都是虚构,只有还原到个人才有意义),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“空拳”。
其次,您说一切“无谓之争”都是因为贝格利教授制造了一个“局内人”和“局外人”的划分,而我掉进了他所布设的陷阱(照您的说法,就连“开明的”巫鸿教授也被这个陷阱迷惑)。在这方面,我和您的看法也是大不一样。虽然,我不见得会同意贝格利教授对它们的使用,即把问题变为局外、局内孰优孰劣的高下之争,但在“内外有别”(对不起,我借用了一个糟糕的政治术语)这一点上,我倒比较赞同他的想法。因为他对学术分歧的存在至少比您更了解也更坦诚,还有我所接触过的很多美国朋友,他们也比较坦诚,不是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。因为在中国这座大山面前,身在此山和身在山外就是不一样,彼此都有看不清的地方。我看不出作为视角的不同,它们有什么讲不得。1980年代,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佛(Lewis R.Binford)批贾兰坡,他也用过同样的词汇(贾兰坡《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若干问题——评宾福德等的新看法》,《考古》1988年1期,77—84转62页。案:贾文所说“宾福德”即宾佛,今多译为“宾佛”。该文引用宾佛1986年的文章《局外人对中国旧石器的观点》“the Chinese Paleolithic an Outsider’s View”,与Nancy M. Stone合写,所谓“局外人”就是outsider)。您的“个体还原论”和“中西无别论”,让我觉得非常矫情(我是按北京土话理解这个词),说句不客气的话,也太公孙龙了。
还有,我想说明的是,拙文讲的话,无论介绍,还是议论,我的基本估计都是来源于同相关学者的接触,而不是光凭书本知识,也不是光凭印象和推论,而且您放心,我们是用中文交谈。我在写作前,同巫鸿教授本人,同他的批评者,还有他的同行,都交换过意见。虽然我也同意,在美国,研究中国早期艺术史的学者,或者狭义的汉学家,他们人数太少,圈子太小,但谁是巫鸿教授的真正同行,我还分得清。在我看来,您的很多估计都是放着眼前说天边,根本不顾事实,特别是争论本身。如果事情真是像您所说,所有问题的引起,只是因为巫鸿教授写了一本了不起的书,然后有一个心怀嫉妒的贝格利对他挟私报复(为此,您讲了一个学术以外的故事),除了他,没人会怀疑巫鸿教授的“众望所归”(那他们还批什么劲呢),说实话,我或其他学者是不会热心这场争论的。
今天我之所以出来编这组译介,而且是费力不讨好地干这件事,这绝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,跟什么人斗气(我很不愿意为此花费时间,也害怕我的朋友会因此受伤),而是因为我和我的西方同行,特别是《剑桥中国上古史》的作者群,在很多学术问题上一直就有严重分歧,而且这些分歧并不像您所说,其实都是由我制造或虚构,而是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私下讨论中,比如“什么是中国人”的讨论,就不能不说是和贝格利教授有关,而且明显已被很多美国学者接受。我认为,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。巫鸿教授也说,贝格利教授的批评目标“是众多的学者和广大的学术传统”。事情绝不会简单到贝格利是自人、巫鸿是亚裔。您干吗非得推论,如果他们把肤色换过来,我就会有另一种评价。我认为,在这一争论的背后,真正成为焦点的,还是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的看法,还是在两大学术传统背后,有很多由来已久的分歧。比如,从最近的断代工程发布会和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看,我相信,真正的争论还在后面,而且恐怕并不是发生在汉学与亚汉学之间,而是发生在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。
我担心,很多本来还能沟通的事,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,还会进一步恶化。关于断代工程和“走出疑古”,我在文中讲了几句话,目的是想请我们的西方同行多注意一下它的学术背景,而不要把眼睛光盯在政治背景上。
为了让您对我所组织的译介有更准确的了解,因而让您能打到我的要害之处(而不是“桌子板凳”),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所采用的写作思路。
(一)我想说明的一点是,我所组织的这组译介其实是想把争论双方的意见摆到桌面上来,让文章本身来说话,不但问题的提出是开放的,问题的结尾也是开放的。至于我个人的介绍,那只是一个引子。它并不是《纪念性》一书的书评,而是对“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”的介绍。这也就是说,我更关心的不是巫鸿教授的书,而是由它引发的这场讨论。我的介绍,当然是面对中外两方面的读者,但我的目的并不是想去教训我的西方同行,而是让我的同胞多少能领略和见识一下什么是“国际学术”。当然您又会说了,这什么也不代表。作为这篇介绍的作者,我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: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,而不是什么具有国际水准或国际眼光的学者。我没有这个资格,也不领这个头衔。而且,我也绝不羞于与我的中国同行为伍,而是按我的真实存在,使用“你们”(或“人家”,或“他们”)和“我们”这样的字眼儿。这就像我反对男人的偏见,但我并不否认我是男人,而且免不了还有男人的偏见一样。此外,我也并不否认,在我的文章中,我有我的立场,甚至还有感情色彩:这就是我既反对国内同行的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,也并不承认西方汉学的很多“天经地义”。虽然为了避免干扰剧目本身的上演,我想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,减少不必要的“画外音”和“提前预告”。还有,当然不用说了,我的英语肯定没您好。
(二)我想介绍这场讨论的主要目的是想引起讨论(有人说是扔炸弹),而不是以一个学术法官的身份对涉讼双方做出裁决。如果您不习惯这种写法,我得请您原谅,因为压根儿我就没有这种习惯,因而也从来不写书评。为此,我故意选择了一个好像行为艺术而且带有刺激性的题目。张隆溪教授跟我说,他对这个题目很不满意,但没有说他的具体意见,我猜他可能也是觉得我太不“国际”,而且每个人从这个词汇读出的可能都是他想读出的恶毒含义,让谁看了都搓火,因而口吐真言,面对面地进行争论,从而达到以毒攻毒,合两偏为一全的效果。虽然我对争论的结果并不乐观。在您的文章里,按照您的角色安排,贝格利教授是偏见的一端,我是偏见的另一端,好像争论是在我和贝格利教授之间,巫鸿教授是这场争论的受害者,您是“隔岸观火”中立而客观的观察者。其实“火”就在您的身边,您也并没有“隔岸”。谁都非常清楚,这里引起争论的是巫鸿教授和他的《纪念性》,而他的批评者是巫鸿教授最直接的同行,他们是一批并非虚构,而是真实存在于西方学术界的很有影响的学者。如果您对我的介绍老是越看越糊涂的话(按您的说法,是我们“越打越乱”),我想向您说明,我既没有想把我的文章做成巫鸿教授的辩护辞(虽然我很同情他的四面受敌,特别是它因中国学术蒙受的不白之冤),也不打算借它来批判贝格利教授(我认为,那样的辩护既无益于巫鸿教授的声誉,也不能使有关的批评者服气)。
(三)您只要不带偏见地阅读,就会发现我是本着这样的用意来安排我的文章:(1)我对中西学术的沟通深感困惑和悲观(参看刘东先生的卷首语),为此,我不但用了“科索沃”这样的新喻,还用了“巴比伦塔”这样的旧典(可惜您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);(2)我用“三岔口”的摸黑对打(可惜您也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)为读者描画了中西学术的典型偏见,让它们出来对骂,好像谁都理直气壮,其实谁都荒唐可笑(我对“人家”的批评比较委婉,而对“我们”的批评比较尖锐,而且是放在前面,可惜的是,您却把我大加嘲笑的说法当成了我自己的说法);(3)我向读者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,并把他们的意见归纳为四点,认为前三点有一定道理,后一点还值得商讨(可见我并不认为西方学者的批评都没有道理);(4)针对上述批评,我想提醒批评者,他们在纠谬订错之余,是不是也能全面和正面理解一下他们的批评对象(我比较习惯于这样的批评),即考虑一下巫鸿教授的写作思路,比如他的后现代倾向和他对中国礼仪的关心,还有最近他对“废墟”的思考,而不要自己跟自己的影子打架,把气撒在中国学术上;(5)我觉得要想消弭分歧,就得勇于面对分歧,知道目前的“国际学术”(我是说研究中国的国际学术),其实还是建立在相互的偏见之上。
这是拙文的提要。
此外,为了供您调整思路,完善文章,请让我讲一下,尊作对拙作有哪些曲解和误会之处:
(1)我讲“三岔口”,关键是说“没有光”,即中外学者缺乏真诚的对话。而您讲“三岔口”是说当事者都是无谓之争,而且对打的不是贝、巫,而是贝、李。
(2)我说的“西方学术范式”,或西方学者“最能认同顾先生”,在原文中都是描述性的,您要反驳我,最好是向读者指出,这里归纳的哪一条是李零所虚构(请参看贝格利讲的巫鸿“犯规”和夏含夷讲的学术“洗礼”),而不必把问题扯到巫鸿做到了什么没有,顾先生是不是也有与西方学者相似的观点。对不起,您好像特别喜欢指东说西,把别人置于没有常识的境地。更何况,我根本就没讲顾先生的观点对不对,他是不是出过国。您一定要把问题归于族裔,那是您自己的事,我并不认为学术传统的差异在于族裔。当然,我还得给您提个醒,您在强调顾先生是中国土生土长、未曾出过国的同时,最好不要忘记,他毕竟是生值风雨飘摇的近代社会,他毕竟是留学美国的胡适先生的学生,虽然我们也同样不要忘记,他还受到过崔东壁式的中国辨伪传统的训练。而且我说“最能认同”,本不过是说,他们的学术倾向正好和顾先生非常投契。这个问题也和族裔无关。比如1929年,美国学者恒慕义(Arthur W.Hummel)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(Arthur W. Hummel,“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”,附王师韫的译文《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》,收入顾颉刚主编《古史辨》第二册,北京:朴社,1933年,下编,421—454页),特别是他的最后一段话,正与贝格利文的最后一段有微妙的相似。
(3)我在文章中曾提到中国学者的傲慢和他们讲的两句话,即“话都说不利索,字都认不全,还做什么学问”。您只要看一眼原文。就不难发现,我要讲的是一种“由来已久的误解”,而且在转述这类陋说之后,马上就是批评。您怎么连我的批评都不看,反而拿它作为我的说法,而且用来挖苦我的英语水平呢?
我觉得,您的最大误会就在于,您常常把我的事实陈述当作我的价值判断,您太不习惯我很偏爱的用事实讲话请读者判断的写作方法,也太不习惯于什么角色也不进入的“无立场阅读”,即像您说的,真的就是坐在台下看。
最后,我向您说明的是,我很感谢您对我们的译文提出了很多批评。但我想请您理解的是,虽然我的英语水平非常有限,远远不能同您相比,但您猜度我是故意添油加醋,巧设陷阱,丑化哪一位,这却未免求之过深。因为您知道,目前在国内做英文翻译,大家经常苦恼的是懂专业的不懂外语,懂外语的又不懂专业,我们的翻译,经常都是勉为其难。这里的译文本来都是请别人翻译,最后不得不推倒重来,或者动大手术。因为我自知能力有限,又听说贝格利教授是以美文而著称,所以除了反复推敲,还请了另外一位现在美国原来也是中国人的朋友(他不愿署名)对译文校了三遍。当然,不管怎么说.译文的一切错误.责任都该由我来负。
您提到我把很多翻译上的微妙之处做了不必要的简化(为了照顾汉语的阅读习惯和便于读者理解,我的确省掉了许多在您看来非常微妙也许不该省掉的小词),还有这样那样的疏忽和误解,我觉得,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意见。至于我译的“由于巫鸿大话连篇,一个定义也不下,读者只好自己费心琢磨他的个案研究”(Offered an assortment of challenging comments but denied a definition,the reader embarks on the case studies thrown on his own resources.),关于其中的“challenging comments”,我还有一些疑问想向您请教。这个短语,我当然知道它在英文原文中是“富于挑战性的评说”的意思,而且这句话,单独去读,并无贬义,但我考虑,此句若直译出来,从汉语习惯,并不容易理解,也比较哕嗦,而且既然它的下一句是“却一个定义也不下”,则反衬之下,此旬当含讽刺意味。我考虑,它是说巫鸿教授在书中讲了很多挑战旧说,刺激想象,打动人心的话,可是没有什么实际内容,也不着边际,所以我把它译成了“大话”。“大话”当然过于直白而且带有否定性,和原文有所偏离。我并不坚持自己的译法。现在我想知道的是,这句话,要是让您翻译,您是怎么译。
以上意见,谨供参考,失敬之处,敬希原谅。我希望您能理解,我和我的朋友刘东,还有很多同行,大家都有一个愿望,就是我们的“交锋”,目的还是为了“交流”(参拙文204页),我们也希望有一种整合为一的关于中国研究的国际学术。当然,它绝不是埃及学或印度学那样的国际学术,而是有广大中国学者参与,并能延续中国学术传统的国际学术,而且正是“为了有这么一天”,所以我才说“咱们还是把彼此的不同痛痛快快讲出来吧”(参拙文214页注②)。
最近,我到美国东部走过一趟,有幸到过您工作战斗过的地方。有一天,,闲来无事,翻看一本美国人讲中国历史的小书,它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都叫“国家主义”(零案:今多译为“民族主义”)。我知道,在美国,“国家主义”是个备受谴责的字眼。我在美国的一个学生给我写信,他特别害怕我被人家戴上这样的帽子。但陋见以为,近百年来,中国的政治家和普通国民,他们虽因饱受列强凌辱,又受邻国刺激,一直在做“强国梦”,它使我的国家动乱贫穷,肯定有很多负作用,但我相信,“强国梦”的根子,还是在于“强国”,“国家主义”的理由也在于“国际”。它和“国际主义”的对立才是最大虚构(事实上,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,也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主义)。
我希望有一天,我们的学术能摆脱这些噩梦缠身的可怕咒语,不管用英文还是中文,大家都能凭学术本身讲话,而且是平等的讲话。这才是我想说的摆脱“巴比伦塔”苦恼的本来意思,也就是说,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用哪一种语言讲话,或者熟练程度如何。
您能体察我的想法,给予“了解之同情”吗?
李零顿首
2000年12月14日
又及:如果您还开课,我的信可以供您做进一步批判。